121期-集體記憶與民間信仰─談頭城老街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活化
陳英豪 / 時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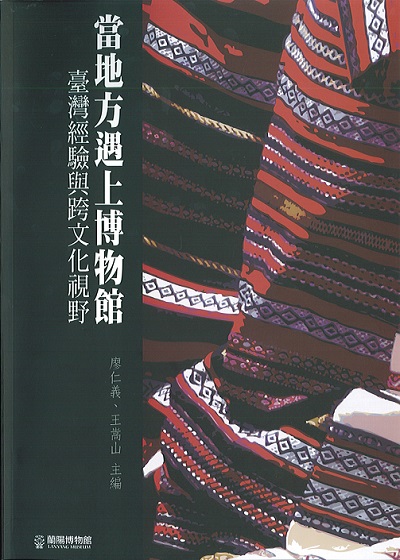
摘要
本篇論文探討民間團體宜蘭縣頭城文化發展協會,如何運用臺灣近二十年來,在社區營造、地方文化館、區域型文化資產的等政策之資源,舉辦結合地方傳統信仰活動的地方新節慶──「千龜來朝」,進行頭城老街文化再造的各項工作,並在過程中凝聚老街居民的集體認同。
在地方集體認同的形塑過程中,集體記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臺灣民間信仰中的文化記憶,影響臺灣漢人宇宙觀、生命觀的認知,並透過祭祀圈的集體祭祀行為維持社會記憶的運作,讓社群共享的溝通記憶成為他們集體認同的標誌。
頭城老街聚落的變遷歷史,與老街南、北兩大祭祀圈發展關係密切,地方上俗稱的「南、北門拚鬧熱」為頭城老街居民共有的集體記憶。近年來臺灣社會快速變遷,「南、北門拚鬧熱」的記憶逐漸集體失憶,傳統信仰活動如龜祭、大身尪逐漸式微,「千龜來朝」的舉辦即是透過文化資產保存、活化及文化展演等方式,重新找回頭城老街的集體記憶與認同。
本文第一節淺談頭城文化協會成立背景,以及現今投入頭城老街再造工作的現況。第二節從「千龜來朝」中兩大文化展演──「神龜選美」與「南來北往顧老街」,描述文化協會如何與地方居民合作各項文化資產保存、活化的工作。第三節爬梳集體記憶相關理論,分析文化記憶、社會記憶、溝通記憶三種層次的關係。第四節從集體記憶的視野,回顧頭城老街聚落與信仰活動變遷之關係。最後一節論述在博物館、文化資產等觀念導入下,民間信仰作為一種集體記憶,在當代頭城老街再造工作中所面臨的課題。
頭城老街再造與頭城文化發展協會
千龜來朝是由宜蘭縣頭城文化發展協會(頭城文化協會),每年向各公、私部門申請經費所推動的地方新節慶,目的在於透過老街歷史與文化的復振,凝聚老街居民認同,達到帶動地方觀光與產業的目的。頭城文化發展協會的成立,是由宜蘭社區大學頭城分班「走讀頭城文化」課程的學員們倡議的,於2006年7月9日正式向宜蘭縣政府登記立案。2007年,協會申請地方文化館政策補助,將頭城老街一座閩南式街屋改建成頭城文化館,該館除作為地方文史的展覽空 間,同時兼作協會在推展各項文化展演活動的推廣基地。
2006年,頭城老街上的北門福德祠與南門福德廟被共同指定為縣定古蹟。適逢政府當時正 推動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定保存與活化計畫,目的是打破傳統單點式的保存方式,而以整體區域環境為保存策略,呼應《魁北克宣言》對於「場所精神」的找尋,將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並重保存,並落實社區參與的模式,讓地方居民參與自己家鄉的文化資產保存行動。為此,頭城文化協會曾與宜蘭縣文化局合作,召開兩場頭城老街再造說明會,一方面為老街居民講解現行文化資產法規,另方面也希望能與居民達成共識,將北門福德祠指定古蹟事件擴大慶祝。
為了呈現土地公廟會的昔日繁景,頭城文化協會將龜祭、乞龜的傳統習俗轉化成慶祝活動,與宜蘭社區大學、北門福德祠(城東里)合作(附註1),邀請街上36家從事飲食業的店家,於2007年3月20日(農曆二月初二)舉行「創意神龜選美活動」,當天凌晨也先依循道教科儀的三獻禮來祭拜土地公,並有其他相關展演活動,將古蹟指定結合傳統土地公信仰,邀集老街居民參與名為「千龜來朝」的地方新節慶。2007年至 2011年千龜來朝已舉辦五屆,除是為了土地公神誕所舉辦的傳統廟會,另一方面也是頭城文化協會在老街進行社區營造、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的年度成果展現。
頭城文化協會投入老街再造工作,也是臺灣近二十年來在社區營造、文化資產工作推動的縮影。2003年宜蘭縣政府委託宜蘭社大,辦理宜蘭縣社區營造員培訓暨輔導計畫(社造員培訓),在頭城文化協會中擔任常務理事的城東里長,當時為頭城城北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即參加該年的社造員培訓,並獲選為文建會社區營造員及社區營造點,以大身尪為主題回到城北社區展開社造工作。城北社區以大身尪作社造的經驗,日後也成為頭城文化協會在推廣大身尪文化的重要資源與經驗。頭城文化協會自2007年以來,同宜蘭縣文化局、仰山文教基金會、蘭陽技術學院及宜蘭社大等單位,合作「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與活化計畫」(區域型計畫)下的「頭城老街 保存活化經營」政府案;也自行以協會名義提出該計畫的社區與民間組織案,進行頭城大身尪文化的傳習推廣;也向民間單位信義房屋的「社區一家」專案,申請三個年度的專案補助推動千龜 來朝。在上述各項專案執行過程中,文化協會確立以傳統民間信仰活動及相關工藝技術,作為頭城老街文化再造的發展方向,持著社區營造的精神與方式,號召居民參與上述計畫案的實際執行。
千龜來朝中的文化展演
每年千龜來朝活動都有一個核心主題,第一屆即為慶祝土地公廟指定為縣定古蹟,由頭城 文化協會、宜蘭社大、北門福德祠發起「神龜選美」活動,南門福德廟方則於第二屆始加入千龜來朝。歷年千龜來朝活動為期兩天,通常選定農曆二月初二的該週假日舉行,並依當地習俗於二月初二子時,兩廟廟門大開讓信徒參拜,依道教科儀三獻禮為土地公行禮祝壽。而為期兩天的千龜來朝,則以「神龜選美」、「南來北往顧老街」(遶境)、「乞龜呷平安」為活動主軸,另有 其他藝文活動、小吃攤、DIY活動來營造廟會氣氛。
一、 神龜選美與乞龜呷平安
頭城本來即保有以龜祭神的習俗,每逢神明神誕各家或組龜會、或自行僱請師傅以各式材料製作龜造型的祭品。而每逢土地公生時,老街南北兩端即擺滿各式龜祭品,祭拜完後即將龜祭品自行分食給龜會成員,或再帶回家中與鄰居、親朋分享食用。因此當頭城文化協會思考以何種方式,來促進地方居民關心、參與老街再造的各項活動,即將此傳統結合他地乞龜風俗來舉辦「神龜選美」活動(圖 1.)。傳統乞龜活動,是由前一年曾乞到龜的信徒,將所還之龜供在廟前,供其他前往乞龜的信徒向土地公擲筊祈願,若得聖杯即可乞得該龜,待日後還願時再作倍數之龜來還願(凌純聲,1972;謝宗榮,2006)。雖頭城老街未有供他眾乞龜習俗,但為擴大居民參與層面,並兼顧活動的親民性,而不讓居民有作龜還願的心理壓力,因此頭城文化協會所舉辦的「神龜選美」,並未有還願作龜之俗,端看居民該年以龜祭神之心意。

相較傳統的龜祭、乞龜習俗,「神龜選美」活動加入評分項目,共分「人氣票選獎」、「最佳造型獎」,以及傳統的擲筊「土地公賞」三部份,試圖兼顧傳統與創新之間的平衡。人氣票選獎佔總分30%,鼓勵參賽民眾邀請親朋好友捧場投票,凡獲得16票即可得該項目滿分;最佳造型獎則邀請評審,依據各項細節的處理評量分數,並要求參賽民眾須附上作品解說牌,解釋創作理念、材料與方法,佔總分30%;而土地公賞則由參賽者至土地公廟前擲筊,基於活動建立在民間信仰的基礎上,此部份佔總分40%,由獲得最多次數者得該項目滿分,若第一次擲即無杯或笑杯則得零分,因此參賽者在人氣票選、最佳造型即使得到高分,卻有可能在土地公賞擲無杯致使分數偏低落選,藉此突顯土地公信仰的神聖性。
依上述三個項目評分,南、北門各自頒發人氣票選獎、最佳造型獎及土地公賞前三名,而南、北門全體分數的前三名再依序頒發金龜獎、銀龜獎及銅龜獎。在活動閉幕式上頒發獎狀,並由得獎作品的作者主持乞龜活動。不同於其他地區是將整隻神龜供信眾乞求,頭城千龜來朝的作法是在乞龜呷平安的分享精神下,民眾乞龜時只拿取龜身部分,龜首與四肢則留給作者本人,其意義為讓神龜來年生肉再次將福氣分享給眾人,民眾也不須於明年再作神龜來還願(圖2.)。而「神龜選美」的每件作品也會附上解說牌,上面寫有作者的創作理念、製作方式與材料,甚至寫上向土地公祈求的願望。居民在以龜作品參賽的同時,也體驗昔日先民祭祀土地公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也創造屬於當代頭城人的集體記憶。

二、南來北往顧老街
當地居民表示,頭城老街兩座土地公廟自古以來並無遶境之舉,活動中的遶境活動始自第二屆千龜來朝。第二屆千龜來朝南門福德廟加入響應,為擴大活動舉行,協會進行田野調查,從中發現可利用的故事與題材。相傳30年前,南門福德廟陪祀的一尊土地公神像,受鎮內某戶邀請去「吃豬公肉」,因緣際會被誤送至北門福德祠,陰錯陽差的就在北門接受信徒的香火祀奉長達30年。協會以此為題材,規劃「土地公南來北往顧老街─土地公回娘家活動」。規劃活動當時曾遭遇南、北門兩邊耆老意見的反對,北門耆老認為土地公像原本就是北門祀奉,毫無道理要送回南門;也有人認為是南門的人不願意承認有神像弄丟這件事,因此不願意北門將此神送回南門;南門的人則表示,南門是持歡迎的態度,是北門那邊不願意將神像送回南門。(附註2)
故事緣由是居住北門福德祠旁的耆老在 2006 年北門土地公廟筅黗時透露的,對於神像究竟是屬南門或北門也無其他證據,頭城文化協會認為這是一個可以「炒作」的新聞議題,因此邀請南北兩邊的代表開會,希望增加遶境活動來豐富千龜來朝活動的內容。當初規劃活動時,因南、北兩邊對於此事有不同的解讀,對於將土地公像從北門送回南門,出現上述的反對與質疑聲音。協會最終採取擲筊問土地公的方式,協會內部表示,若擲筊未得到預期的聖杯,由於北門廟方已與協會取得共識,「土地公說要舉行遶境,就算不能把神像請回南門,遶境一樣可以經過南門土地公廟前,看誰還有反對的理由」,詴圖藉由土地公的神聖性來解決世俗的爭議。(附註3)
頭城老街一向有南、北之分,研究者在頭城進行田野訪談時,對於頭城老街的南、北之分,多位報導人都有相當深刻的記憶,且都表現在對廟會活動的描述上。頭城鎮籍作家李榮春(1911-1994)作品《和平街》中也提到,南、北之分是以慶元宮為分界,南邊以開城孝(城隍廟)、南門福德祠為中心,而北邊則是以東嶽廟、北門福德祠為中心的兩大祭祀圈。根據幾位報導人的說法,慶元宮以南的居民多半是從事密集的勞力工作,而北邊則是地方政教名流的居在地。「以前元宵節時,南、北兩邊會有武龍、文龍在拼陣。北邊的文龍隊員多半較斯文,會身著白色衛生衣,而南邊則較粗曠,即使天氣寒冷,也會打赤膊顯示自己英勇不怕鞭炮」。(附註4)除元宵鬥文龍、武龍之外,地方居民成長記憶中就屬城隍廟與東嶽廟的「南、北門拚鬧熱」印象最為深刻。頭城文化館中也以「南、北門拚鬧熱」為主題,展示頭城老街南、北的大身尪文化。
在南門、北門的歷史紛爭下,頭城文化協會即希望透過南、北和解為主旨,為該尊誤住 30年的土地公舉辦遶境活動,透過輪住兩廟的方式來為增進南、北之間的互動,達到南北和解的目的,因此稱遶境為土地公「南來北往顧老街」。遶境活動中,除土地公神輿前導的北管陣頭與鑼鼓隊等傳統陣頭外,也迎來一隻神龜花燈作為隊伍前導,象徵頭城的精神地標龜山島化作神龜;另有部份的大型神龜作品,會由當地學生以頭城傳統的運貨工具犁仔卡載送遊街,也有扁擔隊負責挑向土地公祝壽的賀禮;除頭城鎮上受邀參創意加踩街各機關隊伍,同時也會邀請其他能表現社造精神與文化傳承的藝陣隊伍。其中由四尊土地公、婆與招財、進寶與五鬼所組成的各式大身尪、僮仔隊伍最為吸晴,各別由當地學生、社區居民親身扛著遶境(圖 3.、圖 4.)。


頭城文化協會在區域型計畫中,陸續與當地神將會合作各項大身尪文化展演的調查、紀錄工作,並進一步與東嶽廟復興社合作,修復與仿製共四尊的范、謝將軍大身尪,並詳加紀錄製作工法與過程(圖5.)。這四尊范、謝將軍身掛「文建會九十七(九十八)年度區域型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專案補助」字樣的背帶,除了參加地方傳統廟會,並與文化協會合作在「2010年宜蘭在地藝術節」中,進行大身尪組裝示範教學以及步伐展演,並由主持人介紹大身尪相關傳統文化,向社會大眾作進一步的文化推廣(圖6.)。在上述以文化資產詮釋大身尪文化的經驗上,頭城文化協會也為學校學生、地方居民開設簡易大身尪製作的相關課程,而這些學生、居民完成的作品平日於頭城文化館蒐藏、展示。待每年千龜來朝的「南來北往顧老街」、或是到友廟交陪,或是其它文化展演活動,即由文化協會動員居民來扛大身尪熱鬧助陣。


文化記憶、社會記憶與溝通記憶
頭城文化協會藉著「神龜選美」、「南來北往顧老街」等文化展演活動,讓耆老口述記憶中的廟會盛況,再度重現在頭城老街上。這樣的盛況是頭城文化協會近年來從事社區營造、地方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的成果展現,過程中同時漸凝聚老街居民的認同感,共構、共享屬於頭城老街居民的集體記憶。今日學界所稱的集體記憶研究,濫觴自法國學者Halbwachs,他認為個人的記憶是建築在社會記憶的框架基礎上,社會記憶是來自於社會的構成,他論證個體是透過社會群體的身分,諸如親屬、宗教、社會階級等,重新定位和回溯他們的記憶(Halbwachs,1992;湯志傑,2003)。
美國學者Connerton(1989)則認為Halbwachs沒有處理社會集體如何進行記憶的傳承,為回答這個問題,Connerton在相對於史學意義上的歷史重構(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把廣義上更廣泛的歷史生產活動稱之為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Connerton 在How Societies Remember一書中,藉由「紀念儀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與「身體實踐」(bodily practices)的分析,探究社群如何有意識的操演過去,訓練社群特有的習慣記憶,並達到傳承記憶的目的。Connerton強調集體記憶的傳授行為,是透過社群不斷操演形成的,使記憶達到體化(incorporating)與刻寫(inscribing),藉由社會實踐、儀式、節慶事件的舉行,傳承社群的集體記憶並凝聚其認同,Connerton也說明社會記憶的最重要價值在於使群體產生集體認同的精神價值。以記憶的體化為例,居民透過集體作龜的「神龜選美」,或是扛大身尪上街的「南來北往顧老街」,都是透過體化的方式傳承頭城的集體記憶。
相較Connerton的觀點,研究古埃及、希臘文明的德國學者Assmann(1995;2006),則從文化、族群的角度,以溝通記憶與文化記憶兩種概念來回答記憶究竟如何形塑集體認同。溝通記憶是指在一有限時間內,社會中不同世代、歸屬的人們互相交換對於過去的解讀,這又以世代記憶為最顯著的例子,因為每個主體成長背景的差異,使得他們對於同樣的「過去」,卻會有各自有不同的記憶。溝通記憶存在於世代之間,當世代不斷的延續交替時,會因記憶的公式化(formulas)與結構化(configuration),形成特定社群、文化、民族所擁有的文化記憶。文化記憶則適當解釋了社群為何以及如何需具擁有時間價值的記憶,Assmann(1995)認為文化記憶提供一個社群認同具體化(concretion)的連結,是一種記憶的指痕(figure of memory),但又會隨著社會在不同世代所遇到現實情況的差異而有所調整。文化記憶因此可擴展至數千年在紀元之間直向傳承,它是集體在不同世代溝通回憶的累積,是整個文化、族群的整體知識,作為文化變遷與創新的先決條件。
集體記憶存在著不同文化、族群、地方上的差異,面對不同社群集體記憶的處理,自然也有各自的分析方式,同時也要連結到特定的歷史、社會背景與有意義的歷史問題(湯志傑,2003:173-182;Confine,1997:1386-1403)。Assmann與Connerton因研究對象與學科訓練背景的差異,注意到集體記憶探討的不同面向。Assmann關注在古代文明的討論,其視野是從過去推向今日,因此其文化記憶的觀點是聚焦在儀式、文字經典化的討論,是探究集體記憶中的哪些“what”經世代累積成為一個族群的文化記憶。相反的,Connerton則著眼今日視野,探究社群如何透過儀式、節慶的重複舉行而凝聚社群的認同,這些社會記憶的“how”如何運作與傳承。不過Assmann並非未注意到集體記憶在當代社會中的具體運作,只不過他將這些記憶運作都視為是文化記憶的延伸,他另以溝通記憶來討論個體、群體在回憶「過去」的互動實踐。相較Connerton關注在記憶的運作實踐,Assmann強調溝通記憶存在於擁有共同經驗、故事、記憶、情感的主體與主體之間,一但這些主體的關係斷裂,這些溝通記憶即將面臨消失的威脅。
文化記憶主導著國家、宗教、族群及文化的歷史演變,也深刻影響集體與個體的孙宙知識及孙宙觀,另一方面藉社會記憶的運作讓文化記憶不斷創新、改變,並具體表現在當代社會中的溝通記憶。以本研究探討主題臺灣民間信仰為例,由於臺灣漢人社會的移民社會特質,學者常以四階段討論各地漢人社會聚落的建立,即渡海、開拓、定居與發展,而在其中皆可觀察民間信仰在聚落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李亦園,1999:285-309)。例如渡海階段,先民要橫越黑水溝面對未知的新世界,因此多半隨船供奉如媽祖、玄天上帝等海神,因此通常也會發展成地方較主要的祭祀圈;開拓階段則常爆發瘟疫,先民多崇祀王爺來保護聚落,因此傳達王爺旨意的童乩也大為流行;定居階段,常因為與其他村落衝突,或是水利上之紛爭,先民多以原鄉之鄉土神來共同祭祀,並發展出相關社群團體(李亦園,1999:285-309;游謙、施芳瓏,2003)。因此可說在臺灣漢人社會中,民間信仰中蘊含的孙宙觀及神靈信仰成為最主要的文化記憶,而相對應發展出的祭祀組織、廟孙、迎神賽會等活動,則作為社會記憶與文化記憶相互依存,而身處不同時代、地區的信仰者也各自發展獨特的溝通記憶。
頭城老街聚落變遷:從民間信仰活動的角度
2010千龜來朝活動主題為「迎神龜、護家鄉」,緣由為頭城「盧孛前池塘」甫於該年初被指定為宜蘭縣定古蹟,但因古蹟土地屬於私人財團,引起一連串古蹟指定的爭議。頭城文化協會認為盧孛前池塘是昔日頭圍港水道的遺址,具有頭城鎮史上無可抹滅的歷史地位與價值,因此應該保存見證頭城因為烏石港、頭圍港航運而興盛繁榮的歷史。該年的「南來北往顧老街」即選在盧孛前池塘出發,由神龜花燈、各式陣頭、土地公婆大身尪與土地公神輿所組成的遶境隊伍,除慶祝指定古蹟之外,同時呼籲居民重視盧孛前池塘的歷史價值(圖7.)。

頭城的開發與烏石港、頭圍港的航運歷史關係密切,並具體地表現在頭城老街兩座土地公廟的創建。約在日本大正年間,頭城出現城隍廟與東嶽廟南、北兩大祭祀圈,逐漸形成成今日頭城「南、北門拚鬧熱」盛況,而南、北之分與相伴而生的廟會文化──大身尪,也成為頭城人共有的集體記憶。不過頭城人「南、北門拚鬧熱」的集體記憶,卻在1970年代因臺灣社會的劇烈轉型,而出現集體失憶的危機,頭城文化協會即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以民間信仰活動展開頭城老街的再造工作。以下將就「烏石春帆」、「南、北門拚鬧熱」兩時期,回顧頭城老街變遷與民間信仰活動的關係。
一、 烏石春帆
1797年(嘉慶2年),吳沙在烏石港南邊正式入墾頭城,頭城成為蘭陽平原地區漢人開發史可追溯最早的地方。1821年(嘉慶17年)設噶瑪蘭廳,並在頭圍街(今和平街)設立縣丞署,烏石港為清政府奉為「正口」,頭圍街因而繁榮。噶瑪蘭廳通判烏竹芳有詵云:「石港深深口乍開,漁歌鼓棹任徘徊。那知一夕南風急,無數春帆帶雨來」,此詵為烏竹芳於1825年(道光5年)選定烏石港為蘭陽八景所做之詵,此時漢人已利用烏石港從事運輸貿易。
但烏石港為一河港,常因山洪暴發而淤積,1878年(光緒4年)發生的洪水就使原本烏石港上游的河道改道,而改在打馬煙出海另外形成頭圍港。1883年美國角板船沉沒,使烏石港嚴重淤積,今僅存烏石港遺址供人憑弔,頭圍港正式接續烏石港的歷史任務與角色(張文義,2003)。然而,1924年(大正13年)8月的一場山洪暴發,頭圍港被大量土石填港,地方俗稱甲子年淹大水,同年11月宜蘭線火車通車,頭圍街的航運轉運角色不再(附註5)。事實上頭圍港填港前夕,日本殖民政府已在基隆興建港口,當時頭圍港的主要航務也逐漸轉移至基隆港再進行轉運,加上蘇澳港的開發,頭圍港大約在1920年代結束其曾為北臺灣重要商埠的歷史地位,同時也對頭圍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重大的衝擊(張文義,2001、2010)。
雖各項資料指出今日現址的兩座福德祠同建於1863年(同治2年),但根據 1836年(道光16年)官發執照指出:
頭圍南門橋、溪仔底、七崁仔等處居民房屋……多有末經領照……查丈間數,造具四至界址清冊,彙詳廳憲外合行給照。為此照給南門仔居民吳換,即便遵照後門四至營業,每年應納衙內福德祠香燈資銀貳錢,屆期送交首事存為香燈之用。(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98:505)
根據1959年的調查指出:
位於頭城鎮城東里係闢蘭最先之路,為當時地勢南北兩端斜出,且有溪川,人民認為所賺之金龍被流出,因此建起此廟,參拜福德正神(土地公)予以阻止(所謂收財)。並於民前49年一月,由當時富翁盧大番創建者。嗣候至民國3、4年時,人民養豬,開金礦等,皆至此廟參香,一時頗獻靈蹟。至此在民國5年4月,由黃炎□發起募捐在此重修。遽聞土地公為土地神,因此至今相信者尚有人在。(臺灣省文獻會,1959)
於老街南段的南門福德祠,同樣為盧大番所建,「民國8年有志者陳合春、林新枝、林心婦、張阿龍等眾獻發起重建勸導階內民眾踴躍捐獻,在於民國47重修至今」(臺灣省文獻會,1959)。從上述兩段文字可看出,兩廟同樣建於清朝同治二年,由於當時老街緊鄰河道因烏石港興盛,在地理風水觀的影響下,居民興建福德祠希望將財氣留住,加上當時因為自然環境有河川流經老街的兩北兩端,外加東面臨烏石港連絡水道,因此由商人盧大番出面將兩廟建立在老街南、北兩端,形成所謂的「街頭街尾土地公」(游謙、施芳瓏,2003)。頭城老街的土地公信仰,在1980年代之前尚保有輪香籤等集體祭祀活動,輪到香籤的居民除到廟內打掃環境、上香之外,會再準備米糕與糖龜等祭品,若是於作牙時間輪到的居民,會準備更為豐盛的祭品。
二、 南北門拚鬧熱
頭城東嶽廟,地方習稱「嶽帝廟」,異於他地,該廟建廟以來例祭非農曆3月28日而是3月26日,其緣由為避開宜蘭東嶽廟撞期而請不到陣頭之故。據傳神像為頭城中崙黃姓先民,自原鄉攜帶渡海來臺後供奉於自孛,因靈驗而有許多信徒前往祭祀。1906年(明治39年)曹姓先民因感恩嶽帝靈驗使其母病癒,出面鳩資立廟並稱「集興堂」,而今「東嶽廟」之名為1929年才有之,該廟於1992年再次重建至今日規模(臺灣省文獻會,1959)。城隍廟內所奉祀城隍爺,原先為水流神像被供奉在開成孝內,後開成孝幾經洪水沖毀再於1868年(同治7年)重建,1912年(大正元年)有童乩湯再三稱城隍附靈,表示多年陪祀觀音佛祖,希望信徒為其獨立建廟。因此地方仕紳出面鳩資興建城隍廟於開成孝旁,始有城隍廟,並在1920年(大正9年)農曆正月6日舉行晉座大典,日後於該日為城隍固定舉行例祭(游謙、施芳瓏,2003)。
兩廟建廟時,日本殖民政府已穩定治理蘭陽平原地區,頭城市街發展也從老街街區向外擴散,換言之,因頭城逐漸形成商業市街,使地方有足夠資金來擴大公共祭祀的規模。簡秀珍(2002:95-133)也指出,日本時代蘭陽平原上原先以土地公為地方祭祀圈代表的村落,因為其他神格較高神祇的香火逐漸興盛,逐漸將這些新興主神視為地方孚護神,並在這轉換過程中更加凝聚庄頭意識,甚至擴及鄰近庄頭。而城隍廟與東嶽廟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因其靈驗性由地方士紳、商人出面蓋廟,也因為兩廟的正式建立,成為頭城地區人群活動的中心。
兩廟建立也與蘭陽地區西皮、福祿械鬥有其淵源,原先兩派的相互械鬥漸轉型成廟會活動上的爭豔。屬西皮派的東嶽廟於1906年立廟,福祿派的城隍廟緊接著在1912年建廟,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1933年頭城街市發展繁榮,東嶽廟大舉遶境,各神將會邀請各地北管子弟團,復興社邀請宜蘭暨集堂,昭義社邀請宜蘭集合堂來助陣;東嶽廟舊名集興堂,原先就是北管西皮派的社團,廟內恭奉西皮派的戲神田都元帥(附註6)。而城隍廟在1934年為紀念改築十五週年,少爺神將會邀請基隆聚樂社,文、武判神將會邀請宜蘭總蘭社與礁溪玉蘭社(附註7)。簡秀珍(2002:95-133)指出從上述記載可看出,兩廟立廟各自與西皮、福祿有關,即便後來在殖民政府統治下兩派械鬥不再,但仍透過與不同子弟會社、神明會的往來而有所區隔。
1922年頭城集興堂東嶽大帝聖誕,開始舉行競賽項目,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如下:「頭圍集興堂東嶽大帝聖誕在二十六日,為此該地之人如例藝閣數十臺、鼓樂數十陣,又放火獅、火馬聯字,及其他奇物藝閣之新式有味者,公堂評定給以優等金牌」(附註8)。1925年又有報導:
例于舊曆三月二十六日,舉祭迎東嶽大帝並迎神輿遊境。本年雖景氣不振然,仍擬舉大祭典。現正由基隆、宜蘭方面聘請音樂團及倩工營造詩意藝閣,商業界亦欲趁此機挽回景氣,各自計謀良策。又有志者林和氏、李文德氏等欲促當事者奮發,並期錦上添花寄贈金牌數面,藉為獎勵。昭義社、興義社、合義社、聚義社、復興社、興安社、智義社、安樂社等神明會。現暗中籌備各欲爭奇鬬巧,是日審查員欲託昔日昔時建築本堂,現雙溪庄長曹天和氏鑑定等級,幸本年宜蘭縣全通,一般參詣者諒必非常雜沓也(附註9)。
簡秀珍(2002:95-133)指出,日本時代蘭陽地區常以廟會、遊藝活動等方式來擴大商機,此時音樂團與子弟會社大為流行,顯示出臺灣社會已培養出專門看門道的觀眾與業餘表演者,遊行隊伍也愈來愈多行業商團加入,藉由贊助活動等方式增加曝光率,甚至頭城地區有因相同職業而組成的神將會團體。藉由行陣、藝閣的評比,也可增加觀賞氣氛並增加與臺灣西部地方藝陣團體的交流,廟會評比的方式也愈來愈嚴密(簡秀珍,2002:95-133)。頭圍此時期也逐漸形成南門城隍爺、北門東嶽大帝二大神誕祭典,而南、北的神誕遶境活動則成為西皮、福祿二樂派拚陣的場域,林蔚嘉(2005)認為也是因為如此才造就頭城地方冥司系統信仰的興盛,而大身尪則為頭城兩大祭典遶境中最具特色的陣頭。
原先兩廟於每年例祭舉行祭典及遶境活動,兩廟巡境範圍大抵相同,以日本時代的頭圍街行政區為主要範圍,大抵同為今日武營、新建及城東、西、南、北四里。昔日由於農曆正月初六先由南門迎城隍,因此北門東嶽的人會先觀察該年南門的陣容,等到東嶽聖誕時就會邀請更多遶境陣頭來熱鬧,而南門也會在下次迎城隍時扳回顏面,地方俗稱為「南、北門拚鬧熱」。約在1960年代之前,南北兩邊的神將會都會相邀參加另一邊的遶境活動,甚至延續日本時代的評比制度搭建審判臺進行評比 (附註10) ,除了受邀的藝閣、北管樂隊之外,大身尪本身的步伐、動作以及服裝也都是評判的重點,優秀者則頒發金牌以茲鼓勵。而也因為這樣的評比方式,使得當年頭城南北兩大廟會活動益顯熱鬧。
目前頭城「南、北門拚鬧熱」已改為兩年各輪辦一次,即今年正月初六迎城隍,同年3月26日則不再舉行東嶽聖誕遶境,而是等到下一年的3月26日才舉行東嶽遶境,而兩邊神將會也不再參與對方遶境。(附註11)
危機、轉機與挑戰:民間信仰視為一種集體記憶
雖南、北兩廟仍每逢兩年各自舉行遶境活動,然1960年代以前存在的審判評比已取消,又因政府以「改善」民間祭典的態度介入,加上整體社會經濟變遷的脈絡,南、北門拚鬧熱不若以往盛況,而尪仔會本身也出現傳承上的斷代危機。1960年代左右的盛況時,東嶽廟下的神將會每逢吃會參與人數大多有30至40人,擔任該年爐主的人則視為神明保佑,爐主在當時被視為榮譽職,並可藉擔任爐主期間的表現獲取會內成員的身分認同。
一、危機
但今日兩座廟宇下的神將會則面臨傳承上的危機,甚至有神將會已解散,其他神將會雖然仍會在每年遶境中運作,但多半都是中老年居多,少有青年人學習傳承。另一方面因為遶境改為兩年輪值一次,過去神將會會成員一年至少可有兩次扛大身尪的機會,但如今卻變成兩年才有一次機會扛大身尪,因此對於扛大身尪的技巧與熟練度降低,也因此影響地方居民對於觀看熱鬧的程度。總之,在技術層面的傳承危機,以及接觸機會的降低,神將會結構愈顯鬆散與無凝聚力,原先被視為榮譽職的爐主如今甚至被視為畏途。會員參與程度七零八落,每逢神誕常都要邀請聘請專門扛大身尪的職業團,而無經費的神將會則由熟練度不高的會員勉強上陣,但因為練習機會少,多數都只能扛大身尪行走,大身尪遶境中最精采的拜廟動作,多數大身尪都無法完整呈現。
頭城老街大身尪文化的傳承危機,同樣普遍發生在臺灣各地,最主要原因是都市化的進程,使得鄉村、都市人口流動情況劇烈,導致地方公廟既有的祭祀圈活動日漸崩解(康豹,2009:287-312;瞿海源,1997:41-76;舒奎翰,2006:85-138)。即使因為功利主義的氾濫,臺灣民間信仰的每萬人所擁有的孝廟數在1970年以後鉅增,但危機卻同樣是來自功利主義的氾濫(瞿海源,1997:41-76)。李亦園(1999:285-309)指出,顯示臺灣民間信仰功利主義趨勢的現象之一,即是滿足個人種種現實需要的意義相對增強。李亦園認為早期移民社會的民間信仰,作為整合人群的作用相當大,地域保護神的角色相對明顯,而共同舉行的祭祀活動所產生意義之於社群團體,則遠遠超過個人需求。但當臺灣邁向現代工商社會,尤其私人崇拜廟宇發展快速,在公廟中的祭祀活動,逐漸由個人儀式取代群體儀式的地位,宗教的社群意義逐漸被個人現實需求的意義所取代。
民間信仰在臺灣社會發展所中的公共性角色與社群意義,強化聚落中人群的連結,發揮抵抗外敵、調解公共事務等作用,隨著都市化進程與功利主義盛行,民間信仰在臺灣社會雖仍顯蓬勃發展,但既有地緣性的社群連結斷裂,個人功利主義盛行,使得一般大眾失去個人對傳統信仰的社會歸屬。另一方面,戰後臺灣政府對本土文化的負面控制,以及民間信仰的世俗化傾向,並成為地方選舉勢力的競爭場域,傳統民間信仰因此蒙上迷信、浪費的污名,社會大眾對於廟會文化觀感也日漸負面,致使民間信仰傳承的斷代危機普遍發生在臺灣各地。
二、轉機
日本時代與戰後臺灣的兩個階段,雖然因為國家權威介入,阻斷臺灣民間信仰與閩粵地區的臍帶,但也因臺灣特有的社會變遷,民間信仰在臺灣的發展逐漸本土化(余光宏,1983:67-103)。而隨著臺灣邁向民主社會,政府開始注意到保存臺灣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正視廟宇作為公共空間在發揚臺灣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時至今日,隨著《文化資產保存法》於2005年修正公佈,各縣市政府陸續指定多項民俗活動,其中如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等七項更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附註12)。
頭城文化協會近年來投入頭城地區民間信仰的文史調查,進一步將採集到的口述歷史、工藝技術,透過文化資產、社區營造的概念促進地方居民的參與,使得民間信仰活動與老街再造的各項工作緊密結合。事實上,頭城既有的民間信仰活動中,每年歲時節慶、神明神誕、遶境、龜祭等民俗,除提供民眾心靈上的慰藉,以及尋求福報與靈驗,藉由上述共同祭祀活動來建立人群網絡與凝聚地方認同。而千龜來朝各項文化展演,即是藉由民間信仰活動既有人群結合的功能,來重新恢復地方居民的公共意識。
土地、東嶽、城隍都源自於古代中國的自然崇拜,歷經千年來的文化記憶之重構與傳承,頭城人在不同時代為這些神明建廟、祭祀,這些神祇的神格與神職使他們具備公正性與神聖性的身分,因靈驗傳說使廟宇獲得有求必應的聲譽,也促使地方頭人、居民更積極參與共同的祭祀活動,並在過程中協調公共事務。例如大正年間隨頭城市街發展擴大,商業活動日趨多元,土地公信仰已無法滿足人們需求,商業與人群活動的差異,也逐漸形成南、北之分。加上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已穩定治理蘭陽地區,面對異文化的高壓統治極需心靈層面的慰藉,財富的累積之外民眾有其他祈願的需求,因此必須崇祀神格與神力更高的神明。而陰司系統的城隍、東嶽大帝除了維持人與鬼之間的和諧關係,並因為具有司法審判、保境安康等職能,也照顧到人們對於社會現實與功利性考量的需求,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
文化記憶中的鬼神信仰為一種媒介,居民在參加迎神賽會的過程也是在參與社會記憶的運作。文化記憶雖有其固定視野,但因不同地域之歷史、環境、人群活動的差異,以及社會現實所面臨的問題,而表現在社會記憶運作的差異上,而參與其中的人們也在這些集體祭祀活動中,形塑出對地方的集體記憶與認同。頭城大身尪文化來自漢人文化記憶中的鬼、神信仰,頭城市街擴大、國家政府的高壓治理,地方人群活動界線的形成,使得大身尪成為頭城人溝通記憶的象徵物,而南、北門拚鬧熱則提供社會記憶運作的一種機制。
對於地方民間信仰活動的集體失憶,頭城文化協會以民間信仰進行老街文化再造,同樣以文化記憶作為媒介,以文化展演的方式─千龜來朝,建構著以大身尪、土地公為主軸的社會記憶,希望讓地方居民在參與過程中再次凝聚地方認同。民間信仰在頭城千龜來朝文化展演的詮釋中,被視為應被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資產,也正因為博物館的公共性,迎神賽會的廟會化為一種新形式的公共連結,透過居民參與的參與詮釋,以及恢復作龜祭神、扛大身尪等身體實踐,重新找回、再次凝聚地方居民的集體記憶。
三、挑戰
地方博物館在詮釋地方信仰文化時,不應侷限在博物館內進行相關主題的蒐藏、展示與教育活動,以頭城文化協會為例,則是進一步將地方文史調查,藉由社區營造的方式擴大居民參與。對於頭城大身尪文化的保存與活化實踐,即是排除居民與之既有的隔閡,並挑選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土地公信仰,製作土地公、婆大身尪。居民除了參與製作過程,也在相關節慶活動親身扛大身尪,更重要的是文化協會利用頭城文化館蒐藏、展示上述土地公、婆大身尪。頭城文化協會也藉著頭城文化館的設置,扮演著政府文化單位與地方的中間角色,輔導鎮內神將會進行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不過大身尪的製作技術終究有其難度,在推廣上如何落實到社區完全參與仍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尤其神將會原屬於私人的神明會聯誼團體,如何讓神將會成員能意識到,大身尪作為一種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性,是目前較為棘手的課題。
另一個根本問題在於,民間信仰在今日世俗生活中的影響程度不若以往,造成居民與民間信仰活動的連結鬆脫,失去個人對於地方溝通記憶與民間信仰中文化記憶的中介。傳統民間信仰因為具有神聖性而受到眾人崇祀,並發揮宗教的社群意義整合地方人群。因此藉由博物館、文化資產的詮釋,讓民眾不再持著迷信眼光看待民間信仰,以及重建民眾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或許是找回民間信仰公共性以及社群意義的適當管道。但也正因為文化資產等觀念的導入,具有神聖性的宗教文物與文化,如何兼顧其原生脈絡,兼納其宗教信仰意義上的真實性,是未來在操作博物館技術時的重要課題。
而在千龜來朝的整體活動規劃上,頭城文化協會除有意識的導入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議題,並將原先散落在居民之間的溝通記憶,像是土地公誤送、組龜會、大身尪以及南、北對立等等,藉由舉辦「神龜選美」、「南來北往顧老街」等文化展演,讓居民在社會記憶的框架下進行記憶的體化與銘刻。而就在每一次慶典與儀式的操演中,形成頭城老街居民共享的溝通記憶,傳承民間信仰中的文化記憶,而地方認同也就在這些層次記憶的運作中轉譯出來。
附註
- 附註1:北門福德祠尚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其管理人由城東里里長擔任。
- 附註2:田野筆記,2010/08/26、2010/11/25。
- 附註3:田野筆記,2010/08/25、2010/12/05。
- 附註4:田野筆記,2010年8月25日。
- 附註5:接續烏石港任務的頭圍港,經常因上游泥土沖刷淤積,地方耆老幼時常被動員至頭圍港區清除淤積(張文義,2001、2010)。臺灣日日新報,1920-06-07〈頭圍港淤塞〉、1920-06-8〈港門復開〉。
- 附註6:臺灣日日新報,1933/04/18。
- 附註7:臺灣日日新報,1934/02/22。
- 附註8:臺灣日日新報,1922/04/22。
- 附註9:臺灣日日新報,1925/04/25。
- 附註10:田野筆記,2010/12/21。
- 附註11:在田野調查中發現, 雖然居民對兩大廟會的輪辦的確切年代眾說紛紜,仍待進一步的田野資料佐證,但居民皆表示在輪辦之後,南、北門雙方仍會互邀對方神將會參與遶境,但某一年卻因為陣頭隊伍序列的紛爭,此後兩廟神將會不再參與對方遶境。
- 附註12: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網站查詢,檢索日期2011/07/01。
參考文獻
- 余光弘,1983。〈臺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孝廟調查資料分析〉《臺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瞿海源主編,頁67-103。
- 李亦園,1999。《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頁285-309。臺北:立緒。
- 臺灣省文獻會,1959。《臺灣宗教調查表:宜蘭地區》。未出版。
- 林蔚嘉,2005。《臺灣神將文化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凌純聲,1972。《中國與海洋洲的龜祭文化》。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康豹,2009。〈戰後臺灣的宗教與政權〉,《從地獄到仙境:漢人民間信仰的多元面貌》,頁287-312。臺北:博揚。
- 張文義,2001。《宜蘭縣頭城鎮烏石港田野口述調查計劃期末報告》。未出版。
- 張文義,2003《河道、港口與宜蘭歷史發展的關係(1796-1924):以烏石港為例》。臺北縣:富春文化。
- 張文義,2010《石港春帆》。宜蘭:頭城鎮公所。
- 游謙、施芳瓏,2003。《宜蘭縣民間信仰》。宜蘭:宜蘭縣政府。
- 湯志傑,2003。〈追尋記憶的痕跡:二階觀察的解謎活動〉《新史學》14(3):173-182。
- 舒奎翰,2006。〈神聖與凡俗的交錯:臺中市東、西區土地公廟的研究〉《民俗曲藝》152:85-138。
-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98。《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三回》,頁504-505。
- 謝宗榮,2006。《臺灣的廟會文化與信仰變遷》,頁206-249。臺北:博揚。
- 瞿海源,1997。〈民間信仰的基本特徵與奉獻行為〉《臺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頁139-266。臺北:桂冠。
- 簡秀珍,2002。〈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慶典中的遊藝活動〉《藝術評論》13:95-133。
- Assmann, J. 1995.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Czaplicka, J. translated. Pp125-133.
- Assmann, J. 2006[2000]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Livingstone, R., translat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fine, A. 1997.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Pp.1386-1403.
-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bwachs, M. 1992. [1952]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In On collective memory. Coser , L.A., (ed. & translated), Pp.37-189.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