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期-早期拓墾與寺廟連結
節錄自《人與神共構 頭城的寺廟信仰》一書
作者 / 陳進傳、楊晉平、陳美暖、游錫財、林雅玲、陳宜伶、黃有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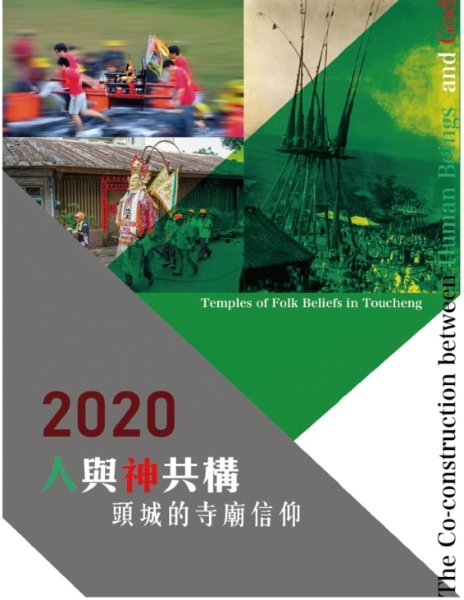
漢人民間信仰確認神靈境界是無比真實,直接影響人們生活,但信眾並不關注超自然體系與神學理論,及其衍生的矛盾,而是在意信仰的神明是否靈驗,即神靈對其祈求保佑、治癒疾病和生育男丁等事情的回應程度。(註1) 這種情形在移民社會的初期更是明顯,因生活艱苦、環境險惡,隨時有喪命之虞。所以他們希望在短時間內得以安頓,免遭流離,減除煩惱,寺廟就是精神寄託所在。
宜蘭漢人開發比較晚近,進展卻很快速,頭城位於宜蘭北端,為移民入蘭的門戶, 由此再向南逐次拓墾,因而不論定居或路過的墾民,備嘗艱辛難堪之際,反應在神明信仰也就特別強烈與迫切,造成早期寺廟興建與開拓過程緊密結合,所以從頭城寺廟信仰可以解讀移墾現象,顯現其在宜蘭開發史上的意義與特色。
一、扼守淡蘭古道的草嶺慶雲宮
慶雲宮位在頭城鎮大里簡草嶺之陽,地當山海交會,坐擁天險形勢,北扼嶐嶺古道咽喉,西守淡蘭古道的山口,東為入蘭海道的要衝。蘭陽開闢之初,為墾民進出蘭陽的孔道,噶瑪蘭設廳後,更是淡蘭官道所必經。自古以來,慶雲宮的創建與發展跟蘭陽平原之開發,息息相關,密不可分,而為拓墾宜蘭歷史的最佳守護神。
慶雲宮的創設,始於嘉慶2年(1797),漳浦人吳明德,捧玉皇上帝神尊渡臺入蘭,歸附吳沙,卜居草嶺,結草廬奉安。道光16年(1836),信眾以其簡陋,為答神庥,爰集資建廟於草嶺腳(今大里國小),稱名「天公廟」。明治37 年(1904),地方鄉紳發起重建,經玉皇上帝選定現址,興築石木結構的廟殿,額曰「慶雲宮」。昭和7年(1932),當地保正倡議重修殿宇,神廟為之煥然。戰後續有增建,擴大規制,使之益形完備。(註2)
如上所言,慶雲宮對墾民影響至深且鉅。先就庇佑移民而言,慶雲宮對墾民保護最多,助益甚大。嘉慶初年,移民為了拓地爭墾,吳沙等移民群眾與原住民時有戰鬥, 互有傷亡,於是就地在玉皇上帝前祈福禱告。從此之後,屢戰屢勝,原住民疑有神助,才罷爭言和。因此,眾多移民艱難困苦的翻山越嶺,涉水渡溪,得以平安到達平地,當然感謝天上神明的保佑,加以祭拜,慶雲宮的香火自是日益興盛。(註3)
宜蘭諺語有曰:「三留二死五回頭」、「過三貂嶺無想某子」,都跟移民經由淡蘭古道、拓墾噶瑪蘭有關。前者指漢人進入蘭陽平原初期,由於交通不便,環境險惡, 颱風、水災、瘟疫頻仍,移民需與大自然和原住民爭鬥,開發過程艱辛困難。所以漢人在開蘭之初,10 個移民大致約有3 個留住宜蘭,2個犧牲性命,5個返回原居地。而後者則謂三貂嶺為昔日入蘭必經之地,當時山高險阻,鳥道崎嶇,加上背負重擔,並有盜匪侵襲、猛獸威脅,因而一旦越過三貂嶺,性命尚且難保,也就無法顧念家中妻兒,只得祈求上天保佑,平安抵達。(註4) 當舉步危艱時,慶雲宮就在眼前,內心的焦慮,消除化解,各種挑戰慶幸過關。簡言之,天公庇護,凡事逢凶化吉,路途安適,開墾順利。

次就守護古道來說,大里簡北、西有嶐嶺、草嶺、三貂嶺,三峰並立,鎖鑰蘭疆,乃蘭陽東北端之天然陸上屏障,大里簡東控海陸之航道,北扼嶐嶺古道之咽喉,控守草嶺山道之出口。因而大里地區舊築之山道有二,一為嶐嶺古道,一為草嶺古道,漢人開墾蘭陽之初,數以萬計的移民由此入蘭。清領至日治,民人、官兵、商旅亦經此以進出淡蘭間。慶雲宮就是扼住這二條古道的唯一門戶。無論上山或下山,均得路過慶雲宮,自然會入廟敬拜,甚至添香油錢,保佑平安。如遇廟殿修建,捐獻者除頭城、宜蘭外,擴及三貂、雙溪、瑞芳,更含括基隆、臺北各地,試觀慶雲宮屢次修建的獻金名單,就是最好的明證。
光緒元年(1875),噶瑪蘭廳改制宜蘭縣,此後至大正年間,淡蘭古道的交通狀況雖無變化,然北宜間舊有的「文山茶路」,兼以劉銘傳的改善,已具產業道路之機能,使北宜交通增加一條通路,但也無礙淡蘭古道的活絡景象。惟此一時期,基隆河上游、三貂山脈之淘金、採金熱潮,及基隆地區之產煤與港埠的形成,造成蘭陽平原與基隆、瑞芳間的人口移動現象,兩地往來仍以大里簡為走廊,慶雲宮就是進出頭城的唯一頸口,直到大正13年(1924),宜蘭線鐵路通車後,情況才有所改變。(註5) 所以在此之前,慶雲宮一直都是淡蘭古道的守護神,保障來來往往的移民過客。
往昔,宜蘭之開發與繁榮,唯淡蘭古道是賴,堪謂蘭地之生命臍帶。慶雲宮已為早期移民善盡護佑任務,功德圓滿。如今時過境遷,功能轉化,更以悠久的建廟歷史、宏偉的殿宇建築,又結合周邊壯麗的山海勝景與豐富的觀光資源,每逢假日,遊客如織,絡繹於途,慶雲宮正是此旅遊區的焦點所在。由是建構東北角觀光特定區,為宜蘭的觀光立縣增添亮彩。
二、異類的移民鄉土寺廟信仰
臺灣是移民社會,宜蘭為此移民社會的翻版。當移民渡海來臺時,首先必須克服航海的艱困,進而通過海盜橫行與風浪波濤的黑水溝,如進墾宜蘭,還要翻山越嶺, 跋涉層巒,此已足激起移民宗教信仰的依賴。後又因水土不服,瘴病肆虐,環境險惡,同時亦須對抗出草獵首的原住民。處在這種生活苦難與生命威脅的雙重壓力下,更引發信仰的迫切感。他們祈求神佛保佑,冀望脫離惡靈陰鬼的侵害,避開一切遭遇的災禍,寺廟信仰於焉滋長,油然而生。最具體有效的,就是從閩粵原鄉的寺廟乞請神佛香火作為護身符,保佑平安。然其所攜帶的香火,會因各自籍貫和信仰不同而有所差異。(註6)
就此而言,形成神明信仰與移民原鄉相呼應,廟宇分布與人口祖籍相繫關聯。因閩粵傳統社會累世繼承,形成以血緣為基礎,聚族而居的地緣與血緣一致的村落社會。臺灣是移民社會,移民渡臺時,難以整個家族遷進臺灣,構成單一姓氏的血緣聚落。所以臺灣民間信仰雖仍有血緣神明的色彩,但更多的是地緣性的保護神,致使漳、泉、粵三籍移民,就祭拜其原鄉帶來的神明。(註7)
臺灣移民信仰如此,宜蘭情況亦大致如是,「蓋緣蘭民三籍,漳居十之七、八, 泉僅十分之二,粵人則不及十分之一。」(註8) 宜蘭平原既以漳州人為主的開發,其地方保護神也具有濃厚的地緣風貌。宜蘭地區計有開漳聖王廟24 座,占全臺開漳聖王廟近4 成,其他如古公三王、輔順將軍、廣惠尊王、敵天大帝等漳籍次要守護神,亦各占全臺相關同寺廟半數以上。(註9)這種移民過程與現象所形成的民間信仰與寺廟興建,在縣內各鄉鎮大致符合,惟頭城地區因移墾路線、開發時間與空間環境的不同,呈現寺廟信仰的特殊現象。
噶瑪蘭大舉開發始於吳沙入蘭,至嘉慶15年(1810),三籍戶口為漳人四萬五千餘丁,泉人二百五十餘丁,粵人一百四十餘丁。(註10)初時三籍相處尚稱和睦,其後發生三次分類械鬥,皆為占絕對多數的漳人跟人數偏低的泉人、粵人及阿里史諸社間的對抗和衝突。結果是:其一,溪北泉人之地盡為漳有,僅存溪洲;其二,阿里史諸社轉往羅東一帶開墾;其三,泉、粵二籍均畏漳籍逞強恃悍,將前分得溪北土地悉行頂賣; 其四,漳人亦藉械鬥之機,進入溪南占墾。(註11) 這種溪北概屬漳人所有的情形,似乎愈來愈嚴重。茲引昭和3年(1928),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的資料,附件表4-1列宜蘭街、頭圍庄、蘇澳庄的三籍人數。(註12)
附件表4-1所示宜蘭街漳人獨多,祀奉開漳聖王就有靈惠廟、三清宮、靈鎮廟、永鎮廟、昭安宮,而泉籍寺廟只有拜清水祖師的光明寺和廣澤尊王的同興廟。蘇澳則是泉州人較多,以致全鎮尚無主祀漳州守護神開漳聖王之寺廟,至於奉祀泉州鄉土神張公聖君、清水祖師的晉安宮、寶山寺,理所當然為鎮內年代較早、香火較盛的主要廟宇。(註13) 相對而言,從數字看,頭城足稱例外,漳籍人口高達98%,泉人比例甚低,為數極少,漳、泉籍如此懸殊比例下,應該是開漳聖王廟多,而泉籍鄉土神廟無由產生。但事實並非如此,頭城地區固然二城里威惠廟和福成里福崇寺供奉漳州保護神開漳聖王,然泉籍鄉土神廣澤尊王也有合興里鳳山廟和安溪人膜拜董真人的董慶寺。而威惠廟雖主祀開漳聖王,廟內亦祀有張公法主,據稱係因械鬥失敗,泉州人離開後,漳州人將原由泉州人所供奉的張公法主迎至廟中同享香火,所以與泉州人也有關係。




廣澤尊王,一曰郭洪福,一曰郭乾,民間尊稱為郭聖王,在飛鳳山修道,並建鳳山寺,後人皆以「鳳山」為廟名,保鄉衛民,治病靈驗,祈求見效,為泉州人信仰神明。相傳昭和4 年(1929),先民奉廣澤尊王在頭城建鳳山廟,供鄉民敬祀。至於董慶寺主神董公真人,行醫修道,惠民救世,後為泉州安溪人所敬祀。嘉慶年間,安溪先賢翁氏奉董公神尊渡海來臺,初在港澳庄設神壇,後迭加擴建,恩賜烏石港居民漁產豐收,出航風順,充分顯現其地緣關係與職業特色。

另據筆者田野訪查所悉,再經頭城鎮民代表游錫財的確認,頭城街上有些住家大廳供奉小尊的廣澤尊王神像,且大多集中在北門地區,大坑里為數亦不少。由於廣澤尊王是泉州的守護神,因此,頭城早期居民應有相當比例的泉州人,只是經過地緣械鬥後,漳州人大量湧入,泉州人成為少數族群,勢力薄弱。職是之故,頭城住民的漳泉祖籍與鄉土寺廟間,看似不相吻合,並無正面相關,有異於其他鄉鎮的鄉土寺廟信仰,實為宜蘭移墾社會的特例。

三、社會組織的寺廟投射
傳統中國社會經過長期發展,使得兩個基本紐帶纏在一起,即血緣和地緣互相結合,共同制約。所以,在地方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不但宗族組織具有鮮明的地緣性格。同樣的,地域性寺廟信仰與祭祀行為,亦與村落宗族密切聯繫。(註14) 簡言之,就是宗族組織在同一地區世代綿延所形成的社會結構。
茲以福建為例,由於福建地域的封閉和方言的差異,使其民眾具有強烈的地緣觀念,聚族而居的歷史傳統更促成地緣觀念與宗族意識緊密相連。反映在民間信仰上, 則呈現地域性鮮明,村落宗族性濃厚,一個村落往往由一個或數個主要姓氏組成,以致寺廟多由宗族出資興建,神明也成為宗族保護神。(註15) 這種長期穩定的血緣與地緣關係所建立的寺廟信仰,傳到移墾社會的臺灣,因時空差異與移民結構不同,造成明顯變遷。雖同樣是地緣,卻已由長期定居,環境熟悉的區域轉移到完全陌生的境域;再說血緣,過去是聚族而居,數代同堂,變為眾多家族之少數人丁的共同群聚。因此, 地緣與血緣,名詞相同,意涵卻全然紛歧。這個區別就是權力結構的轉變,原來長期穩定社會已無法複製在新拓墾區。此時,移民為維持其存在,必須要適應外在環境與社會關係,而人們也會被這些行動的結果所轉化。所以在新移民社會中,當某些人能夠運用此一可能造成差異性的能力去控制外在社會關係時,一種「社會性的權力」, 由某些人統治的社會現象,遂告成形。(註16) 此一差異,非常明確的反映在頭城移墾社會的寺廟信仰上。
眾所周知,寺廟的楹聯,以其材質、捐獻、撰句、書丹、鐫刻等內容,而為重要的宗教史料,並備供地方史研究參考,特別是從署名落款者,可以窺悉當時社會概況。大致說來,幾乎所有柱聯的署名都有頭銜與姓名,但頭城慶元宮的石柱對聯,屬罕見的例外,而是地緣和血緣結合的書寫。茲列落款如次。
- 沐恩吳姓眾弟子仝叩獻
- 賴姓眾弟子仝叩
- 龍溪縣眾弟子仝謝
- 舊南靖迎祥社眾弟子仝叩謝 汪金灶重修
- 新南靖集福社眾弟子仝謝
- 新舊澄邑眾弟子仝叩謝 汪金灶重修
- 新金浦眾弟子仝叩謝
- 頭圍街弟子楊廷選敬奉
- 頭圍街李姓眾弟子仝叩謝 甲辰年李廿五名等重修
慶元宮這種落款方式,在全縣其他寺廟尚未得見,夠得上是特殊現象,尤有進者,更彰顯移墾社會的歷史實情。就血緣而言,開發較晚,世代不足的噶瑪蘭,難以形成同血緣的家族聚落,但在移墾過程中仍能發揮社會整合的作用,惟只能擴及同姓。《噶瑪蘭廳志》曰:「蘭中鮮聚族,間有之,尚無家廟祠宇。故凡同姓者,呼之曰叔姪、曰親人,不必其同支而共派也。其中必推一齒高者為家長,遇內外事,辨是非、爭曲直,端取決於家長,而其人亦居之不疑,一若我言維服,勿以為笑也。」(註17)這種推舉同姓頭人領導宗親執行任務,實屬常態,同治年間,宜蘭的異姓械鬥即為一例。《康氏家譜》中提到:「冬山林、李兩姓,因賭博起糾紛,陳姓居間調節,林姓不允,致陳、李聯合專抗林姓。林玉堂、李進時、陳章各為領首,三字姓之械鬥,廣及蘭陽全境,因此,政府派兵鎮壓之。」(註18)
依落款所言,光緒15年(1889),慶元宮重修時,有3 組楹聯分別由李姓、吳姓、黃姓的眾弟子捐獻,可見血緣關係仍是重要凝聚力量。但要聯絡這些眾弟子,加以整合,收集款項,跟廟方接洽,並非易事,須有同姓長輩頭人出面主持,才能成事。值得一提的是,李姓所奉獻的石柱,到甲辰年重修時,仍是嗣後李姓宗親25 人共同合資促成,可見血緣意識依然深植人心。民國45 年,臺灣省人口普查,上述3 姓人數位居頭城鎮前5 名,其中吳姓還登上全縣第二,僅次於林姓,可見頭城是吳姓的大本營。(註19)畢竟人多好辦事,也容易湊錢,但也要宗親長老帶頭收款,俾利處理贊助任務。
再就地緣而言,早期移居宜蘭的墾民,大多以單身壯丁為主,絕少舉家遷徙。因此,當時人際關係的結合,除血緣外,更重要的靠山就是原居地祖籍關係。蓋墾首們招募墾丁開墾土地與興建水利,常以同一鄉里背景為招募對象。開墾之後,這些同祖籍的人便順理成章地聚居一起,既可互助合作經營農耕,又能團結形成聚落,以抵抗外來的侵害。換言之,早期移墾沒有強宗豪族出現,致使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整合方式,顯得格外重要,比起血緣關係的連繫還要受用。(註20)
噶瑪蘭拓墾之初,吳沙採取「三籍合墾」的辦法,在分地方面,漳、泉、粵各有區域,亦即同鄉聚居型態。這種祖籍分配土地的模式,直到噶瑪蘭設廳後,尚沿用不替,官府召民開墾或築城開河,按照三籍分地墾種與分股施工。在此情況下,同地緣的人利害與共,立場一致,績效顯著。(註21)具體言之,嘉慶年間,蘭地開墾之能非常順利,其關鍵因素是入墾的三籍漢人,雖被稱為流民,但非烏合之眾,而是在嚴密組織「結」下,進行土地拓墾。結是拓墾組織的基本單位,由結首或頭人處理各項事務, 統有數十位墾佃所組成,通力合作,共同開墾某一區域土地,所以結是拓墾組織,亦為社會自治單位。(註22)從而推論,溪北地區的結,雖是拓墾單位,實則建立在祖籍的基礎上。

以此檢視慶元宮楹聯有「龍溪」、「舊南靖」、「新南靖」、「新舊澄邑」、「新金浦」的落款,可見地緣關係已從拓墾融滲到自治及其他事務,當然也包括寺廟信仰的活動。寺廟興建是地方重大事件,每位墾民都希望平安順利,豐衣足食,因而樂於出錢贊助,但個人限於財力,於是結合同籍作伴,合力集資,拜地緣之賜,既能凝聚團結,亦得神明護佑,此時就須頭人出面,號召老鄉,主持任務,發揮多重社會整合的功能。比較特別的是,同一祖籍卻有新舊之別,這雖有先來後到之別,卻也看出須結黨拉派,以維護安全的必要性,否則在移墾社會裡,沒有參與血緣或地緣組織容易受到外界欺侮。此外,祖籍還有「社」的次級團體,如迎祥社、集福社等。這種社的組織,可能就是類似的神明會,而為很好的社會史料,只是要加追究,實有困難,只能期待來日。

慶元宮門柱對聯還有署名「頭圍街弟子楊廷選敬奉」、「頭圍街李姓眾弟子仝叩謝」,以「頭圍街」起筆,表示本土化社會已在成形當中。蓋移墾社會的過程中,血緣與地緣雖為重要的整合力量,尤以初期為然。但隨著時間的延長、空間的擴大,墾民在認同的取向上,逐步超越血緣和地緣的因素,考慮以臺灣本土或移墾當地為認同的目標,肯定臺灣才是自己的歸處,終老於斯的場所,本土化社會也就慢慢浮現出來。換句話說,在意識上,由「漳州人」、「泉州人」、「安溪人」等概念漸趨轉為「臺灣人」、「南部人」、「宜蘭人」等。(註23)頭城竟然在咸豐年間就已有本土化的鑿痕, 雖只是個案,已彌足珍貴,更有其意義在焉。及至光緒15 年(1889),就擴大為一群人, 即李姓眾弟子,可見本土化現象已益加明顯。
如上所述,頭城慶元宮的柱聯上,更早於清代就已顯露記有血緣姓氏和地緣祖籍的捐獻單位,甚至還有「頭圍街」的本土化、在地化的概念,而為全縣境內寺廟所僅見,更是研究宗教史、社會史的重要資料,只是長期以來,無人關注,任其冷落。今特別提點標明,以強調慶元宮在宜蘭開發史與宗教史上的意義和價值。

參考資料
- 註1:易勞逸著、苑杰譯,《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9 年1 月),頁95。
- 註2:草嶺慶雲宮管理委員會,〈草嶺慶雲宮(大里天公廟) 簡介〉(宜蘭,慶雲宮管委會,2019)。
- 註3:徐惠隆,〈慶雲寶殿聽濤聲〉,《走過蘭陽歲月》(臺北,常民文化公司,1998),頁109~110。
- 註4:林茂賢,〈宜蘭俗語初探〉,《「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文化局,2000),頁320。
- 註5:高志彬,《草嶺慶雲宮志》(宜蘭,頭城草嶺慶雲宮管理委員會,1999),頁131。
- 註6:增田福太郎著、黃有興譯,《臺灣宗教信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8),頁101。
- 註7:劉大可,《傳統與變遷:福建民眾的信仰世界》,頁101。
- 註8:姚瑩,《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1829〕),頁57。
- 註9:劉子民,《漳州過臺灣》(臺北,前景出版社,1995),頁295。
- 註10: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1852〕),頁76。
- 註11: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38。
- 註12:石田浩,〈宜蘭村落的形成與其同族組織未發達的原因〉,《「宜蘭研究」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311。
- 註13:邱水金,〈清代蘇澳開發之初探〉,《宜蘭文獻雜誌》,第2 期(1993 年3 月),頁15。
- 註14:劉志偉,〈大族陰影下的民間神祭祀-沙灣的北帝崇拜〉,《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行政院文建會,1995),頁707
- 註15:劉大可,《傳統與變遷:福建民眾的信仰世界》,頁132。
- 註16: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7。
- 註17: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191。
- 註18:《宜蘭康氏家譜》,頁16。
- 註19:陳進傳,〈清代噶瑪蘭的拓墾社會-從血緣、地緣、本土化觀點探討之〉,《臺北文獻》,直字第92 期(1990年6月),頁19~20。
- 註20:陳進傳,〈清代噶瑪蘭的拓墾社會-從血緣、地緣、本土化觀點探討之〉,頁24。
- 註21:廖風德,《清代之噶瑪蘭》(臺北,里仁書局,民國71 年6 月),頁19~20。
- 註22: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頁39~41。
- 註23: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頁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