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期-再說一段南方澳情事
文:邱坤良
週末假期的漁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船隻卜撲卜撲川流不息。一輛一輛的大巴士開進港邊,與停泊在海域的漁船相互輝映。遊客魚貫下車,有的上廁所,有的買漁產,一下子就把地窄人稠的南方澳撥弄得鬧熱滾滾。估算一下人數,這時候散布在建築物、街道與車上、船上的人數大約有一萬五仟人,與三十年前的南方澳在地人口差不多。相同的數字所反映的社會環境與人口變遷卻大異其趣,只有實際在這裡生活過,而且具雞婆性格─愛湊熱鬧、好管閒事的人才會深刻感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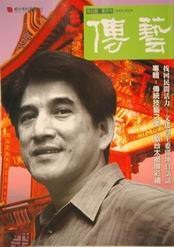
以前的一萬五仟人全天住在南方澳,不管是外地來的漁民,或跑江湖的郎中,生活作息與社交活動全在這裡發生。每個家庭、每個人、每一個商店、攤位、每一艘漁船都是漁港的主人,彼此之間,根脈相連,互動頻繁,共同建構強烈的漁村聚落景象。如今這種特徵逐漸減弱,趕得上「時代」的,就是那幾家大船東與商店,賺錢的更賺錢,無業的繼續無業。「討海」為生、做小工的南方澳人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來的觀光客。目前南方澳的繁華有一大半是靠外來遊客撐著,白天看起來依舊繁華繽紛,一旦遊客離開了,立刻變得空空蕩蕩。尤其夜晚一到,整個港區安安靜靜地,如同卸了妝、準備入睡的漁婦。
來南方澳的遊客愈來愈多,目的不一而足,到豆腐岬觀賞海景、港邊看漁船、享受最新鮮的海產,有的專程來參拜由黃金打造、閃閃發光的金媽祖。當然,也有較具文化感的人,來南方澳作田野考察,用影像紀錄地方風俗、民俗宗教、漁業景觀,或作「深度旅遊」。不管動機如何,最終還是未能免俗,把港邊看漁船、吃海鮮、拜媽祖的「三合一」納入行程,完成「到南方澳一遊」。
愈常在南方澳吃魚、看海的人愈瞭解南方澳「五色人」的特殊性。短短的百年歷史,曾在此生活的族群不知凡幾,猴猴社、平埔族、泰雅族、琉球人、日本人、朝鮮人與來自台灣各地的福佬人、客家人,隨國民黨過來的中國老兵……。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堪稱「八方風雨會中州」。每個南方澳人的外型穿著、語言習慣千奇百怪,各有特色,卻又充滿不同的南方澳味道。

在這個族群多元的漁港,最能印證它的人文與空間特質的,不見得是我這種在南方澳出生的人,反而是南部移民或外國移民。我小學同學有一半是南部人,口音腔調與宜蘭人大不相同,本地人常用怪腔調學他們「俺娘喂!」哀叫。平常大家玩在一起,打在一起,互相到同學家裡做功課,順便品嚐南部漁民的菜瓜麵線、鮮魚米粉湯,這類食物一般宜蘭人並不常吃。他們的風俗也與南方澳有些差異,我最常聽他們講東港、小琉球人「迎王」的故事。小小年紀的我便知道南台灣的五府千歲與我們的媽祖不大一樣,「迎王」的祭典遠比「迎媽祖」大多了。尤其「迎王」時節,家家戶戶擺出琳瑯滿目的食物,充滿每一條巷道,隨香客自由取用,這種善良風俗,令我欣羨不已。

最近南方澳二十位鄉親包了一部遊覽車來台北找我,大談南方澳的陳年往事。乍看之下,每個鄉親都是生面孔,聊了一會,才慢慢發覺有些是同窗,有些是鄰居。幾年不見,大家都老了。帶頭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叫阿朋,小我二、三歲,家裡開鐵工廠,白白淨淨的,個子不大。他說小時候常跟我一塊玩紙牌和彈珠,我已經沒印象了,果真有此事,他大概只有被欺負的份了。
他中學念水產學校輪機科,在以前南方澳人眼中,這個學校很容易混,不太需要考試就能入學。阿朋從水產學校畢業之後,繼承父親的鐵工廠事業,他所製造的馬達機器還外銷到新加坡,賺了不少錢。我當天才知道阿朋擁有發明家的身份,不禁刮目相看。他有多項專利,二十年前還發明一種多功能的釣魚機,贏得瑞士國際發明競賽的金牌獎。
當天聚餐時,阿朋特別發表感想:「南方澳人為什麼特別聰明?這是因為常吃青花的關係。全世界出產青花的地方很多,但是……。」他把眼光掃向在場的每個人,很權威地說:「南方澳的青花最肥。每年舊曆年前後,順著黑潮來到南方澳海面的青花群每隻都是油油油、肥肥肥!皮下油脂有一種DHA屬於不飽和脂肪酸,裡面的OMEGA能促進腦部血液循環,所以人吃下青花以後,不聰明也變聰明。」阿朋這段高論其實已屬老生常談,我都已聽他說過好幾遍了。
他在五十歲那年,自己給自己退休,然後吃飽閒閒,每天在南方澳趖來趖去。他的年紀不大,地方人情世事卻懂得很多。他非常熱心公益,不但參與媽祖廟、社區事務,還打算開一家青花博物館。他有時會跟我通電話,談談南方澳的歷史人文,以及社區未來發展。往往談不到幾句,就會回到「南方澳人青花吃太多,才比別地方的人聰明、會讀書……。」這句老話。

南方澳的人常吃青花魚,毫無疑問,但因而聰明、會讀書,就不得而知了。至少阿朋讀水產學校,就代表他不是很會讀書的料。不過,他是個發明家,必然很聰明。這也證明會讀書或會考試,跟人聰不聰明無絕對關係。否則,單憑高中的程度,如何當發明家。阿朋的聰明,也許真的是吃青花魚的關係。
南方澳一直有三多─—人多、船多、魚多。我跟阿朋念小學那個遙遠、古早的時代,南方澳家家戶戶莫不人丁旺盛,小孩少則五、六位,多則八、九位,一家人擠在一個通舖睡覺。一年到頭,節慶不斷,就是沒有「母親節」、「情人節」這些商業活動。那時候國民所得仍未大幅成長,一般家庭經濟拮据,三餐都很節省。南方澳人不見得每家都吃得起肉類蔬菜,卻餐餐有魚有蝦。魚蝦就跟農家田園裡的菜葉,海裡撈就有,要吃多少就撈多少。
我們成長的年代,家長很少擔心子女的功課,小孩在學校讀書都是放牛吃草、自求多福。每個學生從小吃了不少的青花魚,可是也看不出有多聰明。很多人國小、國中一畢業,就開始工作,男的到漁船煮飯或在鐵工廠做「黑手」,女的學裁縫準備嫁人,或到工廠當女工,而後就結婚生子,不太有機會發揮他們的聰明。
這些年風水改變了,當年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父母,把以前未讀的書都指望子女代讀,對於小孩的功課盯得很緊。這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南方澳人開始「嫌棄」本地唯一的國中、小學,認為它們的師資條件、教學環境不及鄰近鄉鎮的學校。於是,像孟母一般,千方百計把小孩學籍遷移到附近的「明星」學校。有這種想法的家長不在少數,南方澳國中、國小學生人數因而呈負成長,不得不減班。留在南方澳讀書的中小學生繼續比別人多吃青花魚,但在一般教師眼中,他們的成績每下愈況,似乎不怎麼聰明,也難以跟都市的小孩競爭。阿朋一直是死忠派,堅持把小孩留在南方澳念中小學,「愛南方澳,就要相信南方澳,多吃青花,人一定聰明。」

阿明對南方澳的印象其實與我一樣,有種懷舊的情結與期待。他這次帶團到台北找我,是以拜訪「聰明」的鄉親為理由,順便到九份、北海岸幾個景點走走,看看各地的社區總體營造,整個隊伍就像一支進香團。身為社區理事長,阿朋再三央求我多多關心南方澳的事,例如常到母校演講、安排表演團體參加迎媽祖……。
現代的人很難想像會有人住在沒有山、沒有海的地方,我有些同年紀的朋友就有這種「遭遇」。有人從小沒有看過山,也有人未嘗看過海,直到十幾歲轉大人了,才看到山的形狀,嚐到海的滋味。南方澳可是山海環繞的漁港,從海邊往山上走可到蘇花公路,隨海水一直漂流則到世界任何地方。南方澳人生活中最常接觸的就是海水,不論貧賤富貴,男女老少,都能隨時隨地游泳戲水、觀賞海景。走在任何一條巷道上,離海都只有咫尺的距離,差不多每天睜開眼睛,就面對太平洋。
大海早已是南方澳人的生活場景,如同空氣一般,任人吸收。一般城鎮的海灘意象大多屬於情侶之間的浪漫,南方澳的男女老少卻如飲水般,視港邊、海岸如同道路的延伸,整天與海波浪共舞。從我懂事開始,海邊就是朋友聚會談天的好地方,有人服役、出國,或外地朋友來訪,大家必然選擇海灘、港口聚集,望著海上波浪,漁火點點,喝酒抽煙、散步聊天。
天氣晴朗的時候,往遙遠的海面望去,虛無飄渺的天際線彷彿有礁岩般的黑點浮出海面,聽說那就是琉球群島的與那國。從與那國來南方澳的距離遠比去琉球首府那霸還近,更別說日本東京了。以前南方澳漁船不但與台灣各港口交通頻繁,還有到琉球八重山群島的定期船班。顯而易見,這個漁港老早就「國際化」了。我有位小學同學長相與本地小孩毫無差異,也操一口標準的宜蘭腔與極不標準的國語,後來在填寫升學資料時,籍貫欄寫著「琉球」,全班笑翻天了,原來他的父親早年從與那國來南方澳捕魚維生,並且落地生根……。
南方澳在地人這幾年陸續組織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博物館、文化工作室,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想進一步瞭解南方澳的各種面相,包括血液中是否有「雜種」。這些文化志工有很多是我中小學同學、老鄰居,他們三不五時會來電告知家鄉近況,以及他們目前正著手推動的偉大計劃,例如港邊社區營造、漁會歷史空間保存、地方文化館……。嚴格來說,南方澳社會文化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從古迄今,與我這個「旅外人士」無關,我對南方澳的瞭解也遠不及世居於此的鄉親父老,以及正在做社區研究的年輕人。
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是南方澳人,我很慶幸在南方澳出生,在南方澳長大,這是一段珍貴無比的故鄉經驗。

這幾年很多人找我談南方澳事,初見面的非南方澳人與我的談話也常從「南方澳」開始。原因不在我的土生土長南方澳人身份,而是因為我「出名」了,這是阿朋特別強調的。可是我又不是李安或李泰安」,那裡「出名」?阿明說:「你寫《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呀!」他正經八百地說著,順便從口袋拿出《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要我簽名。
《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是我幾年前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內容在追憶一段來自漁港的生活體驗─自然環境、空間動線、風土人情、娛樂消遣。這種體驗伴隨我從鄉下到都市,從年少到年長,影響我「出社會」的生活模式與行為舉止,也累積成為日後研究、創作、展演的空間概念與呈現形式。換句話,《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是講一種感覺,一種心情,一種站在港邊眺望大海的心情。它描繪我的童年生活,也敘述家鄉的文化與空間的觀念。即使步入中老年,南方澳裡裡外外,台上台下的生活影像與情境,仍如走馬燈在眼前浮現。
《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讓我名列「作家」,也變成鄉土歷史專家,與「南方澳問題」專家。許多人認真看待這本書,令我感動。有人把它當小說,有人當地方志、戲院志,或做為「南方澳之旅」的參考資料,按圖索驥,希望找到屬於南方澳人的空間環境與生活動線,或根據書中的人事物串連他們的記憶。有人「研讀」之後,自然而然地認為我在抒發「在地人的鄉愁」,也會認真、熱心地糾正書中的謬誤。
「南方澳大戲院」的老闆首先說話了,他老早就結束戲院生意,但一點也不認輸。「戲院那有『亡』啦?人攏馬好好。」他對「興亡史」的「亡」特別有意見。死亡,畢竟是天大地大的事,也代表人生的大失敗了。有些素昧平生的朋友寄來洋洋灑灑的長信,大談他們幼年在農村、礦區、漁村的生活經驗,這些書信有個共同特點:文筆樸素無華,內容卻深刻感人。每個人的生活背景不同,其實內心深處,都有一部戲院興亡史。

書中出現的戲院、寺廟、人物成為被探討的對象,甚至連我的住宅、家人,都成了被參觀的景點。住在老家的哥哥還因而被仙公廟聘為總務,負責管帳及對外勸募,而他的第一個募款對象就是我:出三萬元為仙公金身添購一件有亮片與金蒼補的豪華披風。我哥哥說:「廟裡的人講,這是仙公託夢指點的!」
寫一本書就「出名」是意想不到的事,我至今坐在台北有冷氣的辦公室裡,還常接到社團「指名」我客串導遊,帶領文化人或文藝營學員追尋老南方澳人的生活空間、提供南方澳最有名的景點,或介紹最「物美價廉」的海產店。久無音訊的朋友恢復了聯絡,電話打來,劈頭就是「我昨天去南方澳了……。」然後霹靂叭啦數說此行的經驗,包括海鮮多便宜,到處都是人、船和車,順便數落一下環境多麼雜亂……。
面對五花八門的問題,我不禁嘆道:「買命喔!」



